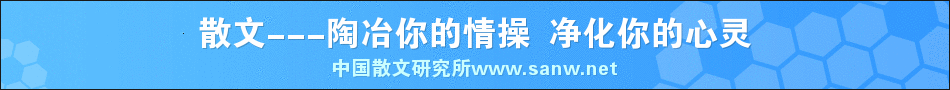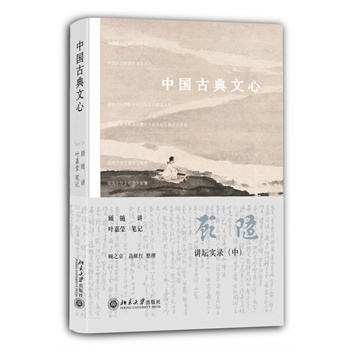余秋雨談散文
我想講一講我自己在寫作過程當中和這個未知結構之間的一個體會。大家知道我這個人是比較多元的人,我曾經講過這句話,我說:我把我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,因為我是個教授;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學術,因為我還寫很多學術著作;我把我永遠想不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散文,我有這個分工。我把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,課堂上你對學生主要還是講你想明白的問題,這和我們今天的演講還不太一樣,我要告訴他們已經有結論的問題。
我們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師,想明白交給課堂。有可能想明白,但是現在還沒有想明白,那我交給學術。學術,大家知道這個論據最后還有一段還叫結論,我通過我的努力以后,我想明白了,想明白不一定正確,大家可以爭論,這是學術。對于有些想不明白的問題,但是我覺得它很重要,又覺得這些問題帶動了我的感情,我還是想不明白,感情帶進去了,我交給散文,我覺得只有這樣的角落,才可能把散文寫好,就是和藝術創作有關了。所以我的散文當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,就是這個問題我其實已經想明白了,那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,有一點想不明白的東西,又牽動感情,這個散文就比較的好一點。
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,我寫第一篇散文的時候的感覺,我原來搞學術,出了好多學術著作,什么時候觸動我寫第一篇散文呢?大家看我的《文化苦旅》就知道,第一篇就是叫《道士塔》。就是敦煌,大家想想看,那么多敦煌的文物,被斯坦因他們都拿走了,出現在倫敦大英博物館,出現在法國的巴黎,甚至出現在東京的博物館里。敦煌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沒有了,很多東西都沒有了。
站在那兒,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,我作為一個中國的年輕的學者,我覺得非常困惑,或者說非常兩難。因為兩個東西都在那兒,因為我知道我們國家兵荒馬亂,如果他們不帶走的話,這些東西可能也沒有了,因為這些敦煌壁畫的洞窟里邊,可能看到了很多燒了煙,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兒,在里邊亂寫。如果這個東西沒有拿走可能也沒了,因為兵荒馬亂,他們好多敦煌的經卷,敦煌的洞,發現以后那些經卷運到北京來,路上這個拿一把,那個拿一把,席子裹著。損失都很大,這個我們知道可能也就沒了。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館,當時得到保存了。
但是我又不甘心,好不容易發現了一百年前,發現了這些東西,都拿走了,拿走了我們祖先了給我們的東西,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,不甘心在哪里呢?就是我們在敦煌發現的同時,我們又發現了甲骨文,甲骨文并沒有讓外國人來研究,就靠我們的學者憑著甲骨文我們研究出了一個很清楚的商代。也就是說中國人還是有研究水平的。我們還有能力保存它的,但是兵荒馬亂太嚴重,在那么遙遠的敦煌,保存可能又很小,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,大家理解我這個困惑嗎?我不知道該不該拿走,我是個世界公民,我不認為當一個強盜,我如果他是帝國主義強盜,我這篇就寫不好了,因為這很簡單,帝國主義強盜拿走了我們的文物,我們一定要把它拿回來,這個文章就寫不好了,因為我這里面有未知結構,沒有兩難結構了,大家理解我這個意思吧,沒有兩難。如果說我另外一個結論,應該拿走,這個財富是全人類的財富,拿走做全人類的保存多好,我這篇文章也寫不好了,因為我心里沒有兩難,拿走就好了。現在好多青年學者說應該拿走,但是我的心中不是這樣,我既不認為他們簡單是強盜,他們也是學者,他們不是強盜,但是我同時又不認為他們應該拿走,當我兩難的時候,我當時突然出現一個圖像,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話,我如果知道這個事情的話,我在沙漠上會攔住他們的車隊,我會和他們辯論,這是我們祖先的遺產,你們如果好是心的話,有沒有可能幫幫忙運到北京,我們那兒有好多學者,和他們辯論。
但是當時也有好多東西運過來了,路上丟失那么多,北京也沒有很好的保存機構,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又矛盾,如果真把這個車攔下來了,他真交給我了,這是當時幻想了,我把它拉到哪里去?我拉不到哪里去,我不知道把他們放在哪里,攔下來的車隊我讓他放在沙漠里,我一個人只能蹲在沙漠里,大哭一場。我產生這個感覺的時候,我覺得一篇好的散文出來了,因為兩難出現了,大家理解我這個寫出的感覺嗎?我覺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場的時候,我覺得是一篇散文,我散文寫作的開端,就是這樣來的,而不是一般的寫作。所以我一看到中學生的好多寫作簡單就是這樣,他們是帝國主義強盜,中國水深火熱,他們還趁火打劫,這個不是一篇好散文,文章也可以,不是一篇好散文,倒過來應該拿走,人類共同財富,我們為什么要保存它?好,這也可以,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,因為它不牽動人的感情,它沒法出現兩難所造成的一種均勢,就是均勢。現在世界越來越開放了,覺得我們現在能夠把巴黎和倫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。我們都拍過來,我們的學者研究得很好,心理很平衡了吧,是心理可能平衡一點,因為我們可以讀解它,也可以擁有它。
但是我這次到了希臘
相關閱讀:
|
讀完這篇文章后,您心情如何?
|
網友評論(共有 0 條評論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