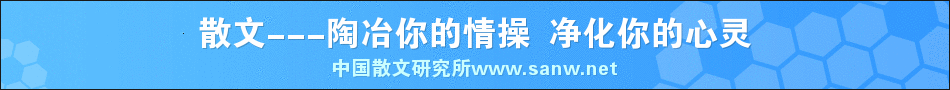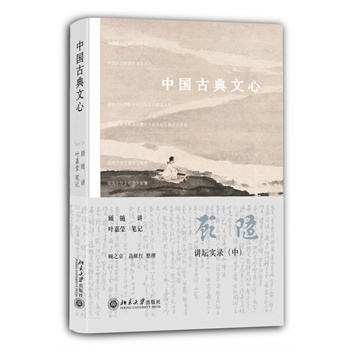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
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
傅查新昌
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
在中國西部,一直存在著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。
西部這片土地,作為一批批作家詩人充盈生命內部的自然品質,作為闡釋人類生存活動的飛跨形式和廣闊的寫作空間,無私地賦予靈感這個既柔順又暴力的尺度。一批批作家詩人的特殊視角,好斗的挑戰姿態,在一種對文化身份認同造成的壓力,以及對緊張狀態的調解之后,隨著極度無意識狀態下的深入思考,經歷了一場認知能力的提升,審美經驗的積累的復雜過程,并從不同層面介入文化中心的權力話語,逐漸形成多元格局和個體性話語的書寫策略。
就當代而言,多少不敢自敗于筆耕的西部小說家、散文家和詩人,以不同的個人體悟、經驗、情懷和態度,挺進中心話語和各種話語的矛盾交織處,直面被文化體制掩蓋下的話語霸權和身份排斥,重新審視物質時代與文化表征的互動。在文化身份認同的激烈競爭中,有些人一舉成名,成為一方文化霸主;有的盲目而溫順地滿懷世俗心態的書寫焦慮,急功近利地在文學道上苦苦掙扎;有的長年累月處在無名狀態,在求解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中,拋棄本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質,任意放逐自我,走向價值平面的意義滑動,觀念錯位的困境,最終成為心靈流亡者,成為狂妄自大的寫作瘋子,成為喪失人格的精神侏儒。對這種嚴峻的不祥后果,人們應當姑息遷就。然而,怎樣對當代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,進行一次公正的審美判斷與學術闡釋,怎樣揭示西部作家詩人所體現出來的文化精神的內在變異,怎樣透視一批批作家成功背后的迷惘狀態,對于批評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。
用現代性的審美眼光,反觀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過去,卻不無令人驚喜之處,不同時代涌現出了不同層次的作家群。二十多年前,以楊牧、周濤、章德溢、昌耀、林染為代表的“邊塞詩”,像一陣強勁的西北風,震撼了中國大地每一個文化角落,他們懷著高昂的愛國激情,選擇了狂熱時代的抒情形象,并為這特殊時代的選擇,付出了熱情錯位和嚴重表征危機的代價。“邊塞詩”是在地域性、民族性和國家意識的過分強調中,表露出其詩情膨脹、詩意空洞和文字游戲的特殊意義。一個把謊言作為生存條件的時代過去后,這批善良的抒情詩人經不起現代性的挑戰,在主導話語嚴密網絡的總體控制之下,集體喪失了對個體獨特性的思想更新與精神維護,最終成了被新歷史語境反諷的枯枝敗葉。但是,在“邊塞詩”疲憊尊容的背后,路遙、陳忠實、張賢亮和賈平凹這幾個典型人物的小說,在中國是最領風騷的,給讀者和社會帶來巨大的震撼,成了說不盡的議論焦點,百看不厭的文化景觀,甚至把一些作品視為頹廢的結果,沒有進行公正的審美界定。
無論如何,正當中國人懷疑一切文化現象的時候,現代化已變成世界惟一的未來之路,市場競爭、目標焦慮和技術瘋狂,成了這個時代的全部文化表征,而文學仿佛變成了荒原上的最后一棵小白楊,成了作家詩人們用來裝點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已。在多元價值觀激烈對峙的特殊時期,路遙的《平凡的世界》使道德存在了沉重的審美意味;陳忠實的《白鹿原》以其宏大敘述的思想魅力,大膽表達了深切的價值關懷和人性探索;賈平凹的《廢都》使精神品質成為當代人生存需求的奢侈品,以其頹廢道德、煸情伎倆、語言浮腫和思想干癟,暴得大名并引起廣泛爭論之后,成了一部通俗文學的經典小說;周濤以從詩歌到散文的轉達場寫作,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,一舉成為西部散文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。然而,在同一個文化層面上,詩在最純潔的偽詩道德異彩中日益貶值,一些具有欺騙意志的西部詩人,以及那些個悟出什么的鐵碗人物,開始以輕淺謔浪的文字游戲,替代了昔日那種自認為崇高的價值關懷。在一種冷漠的隔世心態中,伊沙用隨意捏把的至尊意象,以本真意識和頹廢情懷,寫出了那首著名的詩《餓死詩人》——這是破天荒的文化大事件。從此,詩人成為惱怒的多余人和麻木的局外人,詩人的詩學立場和詩藝探索,從生存焦慮向文字游戲轉位,生命的創作激情,成了世紀末文化的一個玩世不恭的遺夢。
在后現代的沖擊中,使當代西部作家詩人在產生思想震撼的同時,為了把心靈鴻溝變為生存坦途,在受施者般顫抖中開始了明顯的創作轉向,因為他們越來越清楚這樣一個事實:無論喜歡或接受,反感或拒絕,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跨越國家和科學界限的文化現象,已經無可避免地引起目光銳利的西部作家詩人的思考。而且,最引人注目的是,西部作家詩人的創作確乎完成了三大轉向:敘述與結構的轉向(從陳忠實的《白鹿原》式的宏大敘述,到寇揮的《想象一個部落的湮滅》式的世俗關懷);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轉向(從賈平凹的《廢都》式的時尚著述,到唐卡的《你是我的歸宿》式的姿態表演);身份認同與創作目的轉向(從周濤式的詩歌創作向散文和小說的轉場寫作)。這種話語轉型、價值觀轉向和轉場寫作,用今日的審美眼光來看,在總體上既有積極的價值因素,
相關閱讀:
|
讀完這篇文章后,您心情如何?
|
網友評論(共有 0 條評論) |